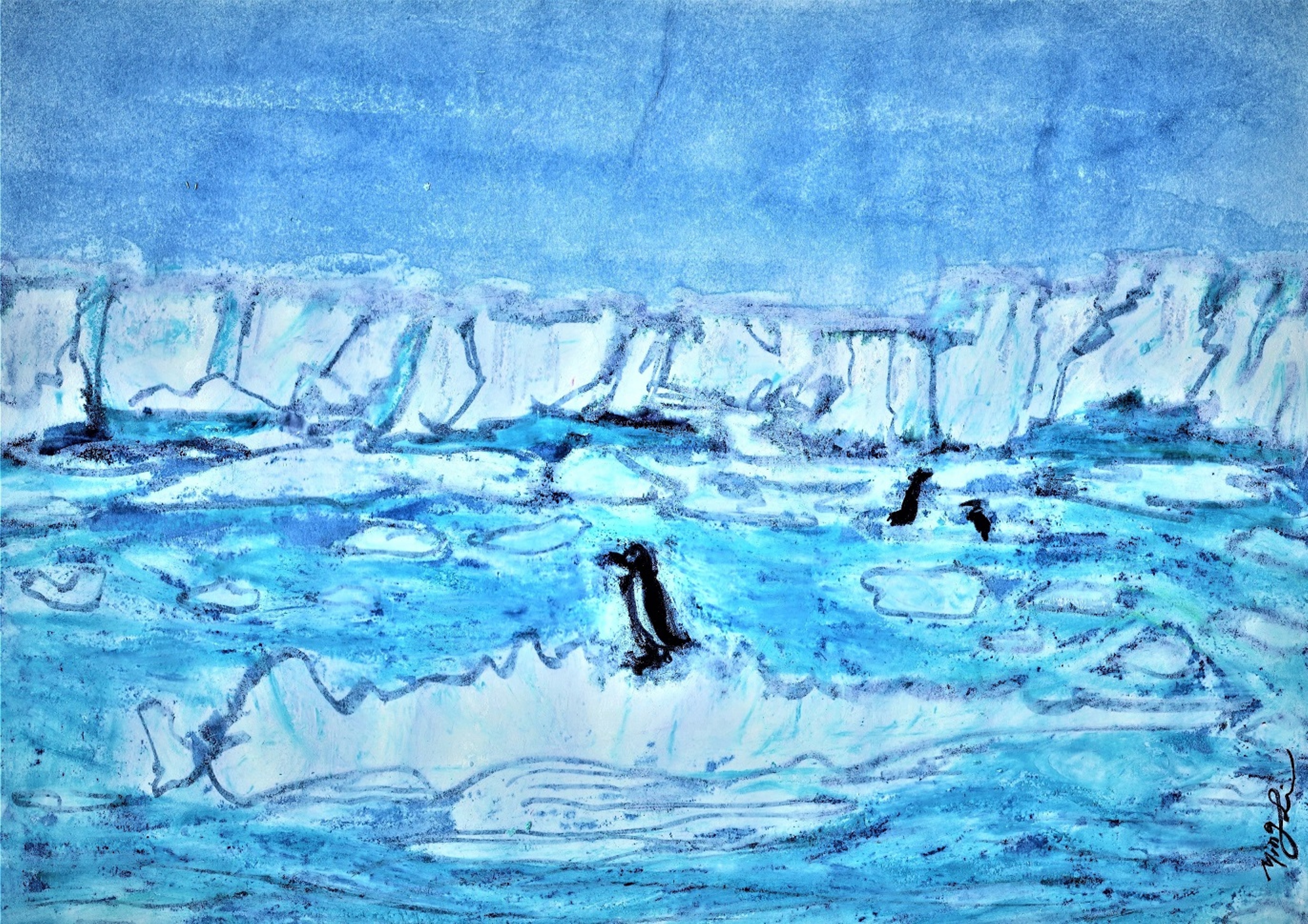文/攝影 翁少非遊覽車從林芝爬一上午的山路,越過白雪皚皚的米拉山口,來到拉薩地區的墨竹工卡,車子停在檢查站旁,導遊和隨車的公安下車去辦理通行手續。米拉山是藏民心中的神人山,適才在海拔5013公尺的山口停留拍照,正好也測試了高山症的反應,幸好只有一兩位團員輕微頭痛,大家對後頭十多天的旅程就較安心了。從這兒到拉薩,還需四五個鐘頭的車程。在等候導遊和公安上車時,許多人閉起眼休息,車廂靜默了下來,而你,把眼睛貼在車窗,凝視窗外的景觀,試著瞧出些什麼的。人生有幾回,可以勇於離開家鄉千里,到遙遠的邊陲地帶探險。林湘萍《誤闖西藏的輪迴》裡說,「生命總是容易在最熟悉的地方迷失,卻會在最陌生而純粹的所在找到出口」。西藏正是你夢寐以求、最想來卻不太敢來,最神秘的陌生之地,在此若能找到生命的出口,這個出口又會是什麼?之前,你去葡萄牙的埃爾瓦什,最想看的是她的橘風情;去西班牙懸崖之城龍達,最想尋覓的是海明威印記;去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最想喝杯《北非諜影》裡的瑞克咖啡;去美東的華爾騰湖,最想在梭羅的林中小屋坐坐。這些的想望都跟你偏好異國情調的浪漫以及緬懷心儀人物的行跡有關。這次到西藏,跟以往大不相同。西藏位處世界屋脊,平均海拔約四千公尺,高極的氣候地貌,給你一種孤冷空寂感,而處處可見的風馬旗經幡、瑪尼堆六字真言、冥想酥油燈,除卻了世俗的功名利祿,讓你收斂嘻皮笑臉,簡單了繁雜的心緒。也許是把心放任成無根的浮萍,才會將眼前所見的移動都看成在流浪吧!遠遠的,有一個小黑點從路的那端走過來,是哪種小動物在流浪呢?幾年前去新疆,遊覽車好幾次在主幹道上停下來,等候一群群的羊過馬路,會是黑頭羊嗎?但,看身形又不太像。 這條土石路還在修建,兩車道的路面還算平整,路的盡頭是山脈的宏偉背影,初冬的陽光伸出胳臂沿路撒暖,路旁那排高大的白楊木把影子拉長,幫路畫上等格線,這個小黑點就像小時候放學後的你,數著碎石的影子踩,走兩公里多的路回家。呀,是一隻藏香豬。怎的?就一路的走過來,孤獨的身影寂寞的走在馬路,不理會扣囉扣囉路過的車輛,不理會滾滾揚起的灰塵,逕自往前走。令人吃驚的,牠好像認識你,而且,好像是趕路來跟你見面,竟然來到遊覽車旁,在敞開的車門前停住腳。莫非這是前輩子注定的約會,你連忙跑到車門跟牠照會。牠仰仰頭,長長的鼻子呼著氣,用深邃的眼神回望你。牠鑲在額頭中央的那撮白毛,像張開針羽的花卉,這般的靈氣,難道曾是仙佛的座騎?動物跟人類一樣有感情和靈魂。動物界的學名Animalia源自拉丁文「會呼吸的」和「具有靈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也把動物的靈魂,分成理性靈魂和感性靈魂。而你,曾在楠西密枝的農莊,看過一隻紅冠公雞在前、母雞殿後,帶三隻小雞排隊,安全過馬路的經過;也飼養過一隻會跟你互道您好、停在你肩膀哼歌的八哥。聽聞藏香豬智商高、嗅覺靈敏,能找到人類找不到的珍泉。這隻小豬若是為了找珍泉,就像小時候老是想要到上山尋靈藥的你;若是為了來跟你會面,那這可是你這輩子的大事,這意味著你的生命不僅是今生今世,而且還跨界跨世的呀。導遊辦妥手續了,車子繼續往拉薩前進,藏香豬的身影逐漸縮小,直到在你的眼簾裡消失,你才回神過來。你把拍到的照片拿給同行的小白看,說:「也許,我上輩子是藏香豬。」小白先是露出訝異的表情,而後莊嚴的說:「輪迴嗎?也許,這只是一個巧合。也許,牠不是來看你,而是來看我,而我錯失了這次緣分,我倆得再修個幾百年。」不知怎的,你想起《西遊記》裡的沙悟淨,原本是天庭武將,後因失手打碎琉璃盞,被貶到流沙河當起妖怪,後協助唐三藏取經,又修得羅漢。在西藏,面對肉體的生滅總是從容,不急著完成些什麼,這輩子沒做完的,還有下輩子。肉身只是靈魂的暫居處,得要行走一段不生不滅的旅程。是麼,在西藏,偶遇這隻流浪的藏香豬,你靈魂的旅程就隨之長遠了起來。